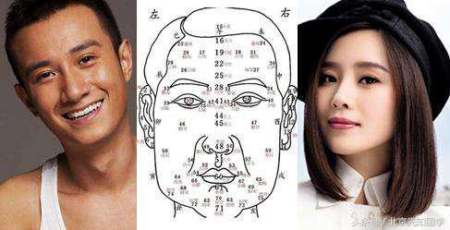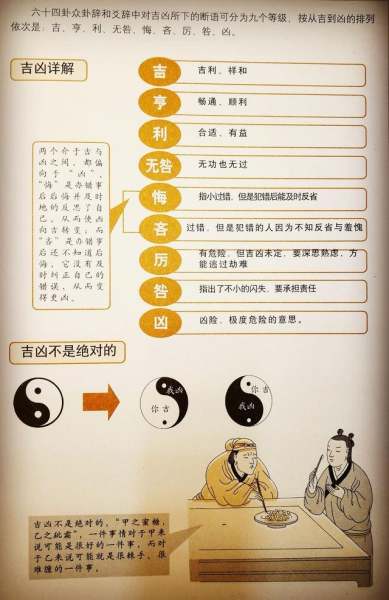她被快递员撞飞,昏迷20天后,50万治疗费该找谁要?
来源:国际金融报
2020年11月16日23时15分左右,看似没有任何交集的两人打了个照面。
彼时,张兰(化名)是巴菲特名下一家投资类子公司员工,正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学院攻读MBA。那晚,她骑着单车,被迎面而来逆行的盒马骑手李小鹏(化名)当场撞飞,头部严重失血,立即失去了意识。
撞人后,李小鹏并没有逃逸,而是和路人一起报警将张兰送至医院。李小鹏随后停工,在经历了惶恐、不安后,当年12月,盒马通知他返回工作岗位,张兰则进行后续的治疗。
20多天后,张兰苏醒,交警告知她,上海电瓶车大事故的肇事者逃跑率是50%到60%。张兰不由得感到庆幸。
交警随后给出了交通事故认定书,裁定驾驶员李小鹏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五十七条。根据裁定书,张兰前后50万的治疗费,应该由甲方当事人,即李小鹏一方承担。遗憾的是,李小鹏赔付了3万元后再也无力支付。而盒马,以及李小鹏作为众包骑手的“名义雇主”上嘉物流自始至终均未露面。
李小鹏来自山东,今年45岁,一副老实巴交的农民模样。就像很多众包骑手一样,他没念过什么书,小小年纪就开始出来“闯社会”:他先是在广东打工,后来到东北挖煤,一个月工资在五六千元左右,之后又辗转来到上海,20年的打工生涯一晃而过。
李小鹏给张兰看了自己的工资单,盒马的名字自始至终未出现在任何纸面上。对于这样一位打工人,张兰没有强行要求他支付医费。在这个故事里,被撞者和撞人者并没有呈现出针锋相对的关系,更多的是无奈。
在偶然的机会下,张兰发现,李小鹏无法说清楚劳动合同意味着什么。张兰不禁陷入深思,为什么(外卖行业)没有劳动保障和共担机制?为什么很多遭遇意外的快递人最后都放弃治疗?行业规则能不能进化一下,优先保障生命?
在熟人建议下,她欲将李小鹏、盒马,以及配送商上嘉物流送上法庭。
“骑手”的无奈
2015年,身在上海的李小鹏在街上偶然看见了盒马的门店,当时他直接在现场跟人聊,门店的人随即将他推荐给了第三方用工公司——上嘉物流,只这两步,李小鹏轻松成为一名众包骑手。
和很多外卖骑手一样,李小鹏知道自己是一个“基层人士”,盒马为每个门店配了主管。“平时不太能见到他们(主管),恶劣天气的时候也许会露面,鼓励大家坚守岗位。”李小鹏说道。
2020年初,李小鹏换到上海市另一个区的盒马门店,原因是听说众包骑手不太安全,在新换的门店里,李小鹏的身份是“专送骑手”。后来事实证明,这一身份的转变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。
在外卖行业,上嘉物流这样的公司也被称作配送商,是李小鹏名义上的雇主,但他从未与上嘉的人接触过,在为盒马工作的几年里,李小鹏的支付宝每月会定时收到工资,这些工资由江浙一带的公司汇入,上嘉物流和盒马隐于幕后。
在盒马,无论是当众包骑手,还是后来转为专送骑手,李小鹏都未与盒马直接签过劳动合同。
一位美团外卖员告诉《国际金融报》记者,在美团做众包骑手,骑个电动车、拿个头盔就可以上路,也不没有强制的上下班时间。而做专送骑手就意味着全天候的服务,并不自由,不过平台一般会给专送外卖员买上保险。“有保险,一天会扣三块钱,每天手机上都有提示”。
然而,这点微薄的保险是远远不够的。
“被保险人数量庞大、总保费金额高,上千万元的保费并不罕见,给用人单位带来了极大的人力成本。尽管总保费高昂,但保险公司在此类项目上的利润率极低,甚至是负利润,原因是这部分特定人群出意外的风险太高,保费自然也就高。这又与企业‘低保费、高保障’的想法相冲突。”某家保险公司的精算师向《国际金融报》记者表示。
提到外卖员,很多保险公司的第一反应就是“没得赚”,一些公司为外卖员推出的计划实际上保障都很少。“只有这样,保费才能降下来”,对于一些规模较小的险企,保险公司一般都拒绝承保。
而对于平台方,用人企业一般给外卖员上的是疾病保险,而非意外险。有这方面意识的外卖员会给自己买意外险,几百块可以保一年,大部分快递员会嫌贵。
用工关系层层外包
李小鹏和两年多前出事的饿了么骑手邵新银一样,他们为外卖平台送单,但在法律上,却不直接和外卖平台发生联系,邵新银后来被医院判定为9级伤残,在起诉的时候,前来应诉的是他从来没听过的公司——迪亚斯公司。
诉讼期间,应诉的公司越来越多:太昌公司、天津某建筑公司、上海某外包公司,这些公司都曾给邵新银发过工资、缴过税。然而直至今日,邵新银还是没有拿到医疗赔偿。
配送商是支撑起庞大外卖行业的重要一环,如迪亚斯、上嘉物流等。
中国裁判文书网显示,上嘉物流身负多起官司,其中多项为劳动合同纠纷,三项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,三项以原告撤诉终结。
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教授、利物浦大学副校长席酉民告诉《国际金融报》记者,从管理角度来讲,因社会趋利避险行为,一些机构会在法律体系面前“打擦边球”或寻找漏洞,这无可厚非。遗憾的是,这种博弈使得弱者在各方面面临挑战和风险。一方面,需要完善机制来促进,这个过程会很漫长,另一方面则是多方博弈形成妥协方案。
“但到目前这个程度,已经不是管理的问题了。”席酉民说。
对此,北京致诚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徐淼深有同感。她向记者解释外卖平台的用工逻辑:在平台刚开始兴起时,骑手与平台签订的还是劳动合同,随着平台急速扩张,用工形式也跟着迭代了。
截至2020年,我国外卖市场规模达到6646.2亿元,同比增长2965.6%,2020年共享经济参与者人数约为8.3亿人,其中服务提供者约为8400万人。在这段时间里,外卖骑手的劳动关系开始裂变。
十余年前,外卖平台刚刚兴起时,平台主要以“平台自行雇佣骑手”或“劳务派遣”的用工模式为主,此为“传统模式”。这个时候,骑手与平台的劳动关系还受到劳动法的全面规制。
几年后,“众包模式”介入了,一开始,外卖平台往往会直接招募众包骑手,见证了这种红利之后,外卖平台开始与众包服务公司直接合作,将其本应承担的成本和风险转嫁给众包服务公司。
记者从致诚律师事务所处得知,专送模式和众包模式出现的同一时期,外卖平台开始大规模调整骑手的“编制”,联合配送商将传统模式转为“表面外包、实质合作用工”的专送模式,随即演变出网络外包和个体工商户外包。
{image=1}
徐淼告诉《国际金融报》记者,目前骑手的劳动形式主要集中在5、6、7、8。
“至于李小鹏为何会收到不同公司发来的工资,据我们了解,外卖平台是把招人这回事外包给配送商,而配送商又把发工资这回事外包给了其他公司。”徐淼表示。这样做的目的是进一步稀释劳动关系,“平台压着配送商,配送商压着骑手”。
徐淼向记者表示,众包的工作模式还普遍存在于餐厅服务员、医院清洁工群体中,但对比其他行业,外卖平台将这种形式用到了极致,在“平台经济”的驱使下,骑手们没有议价能力,无论是外卖平台将配送业务“外包”给配送商,还是配送商进一步将业务“转包”或“分包”给其他配送商或灵活用工平台,其实质均是相关主体的合作用工。外卖平台以直接(App)或间接(配送合作协议)的方式制定专送骑手的工作规则,是整个用工模式的主导者,配送商实际上合作控制着专送骑手的劳动过程,这样才有了“困在算法系统里的骑手”。
醒来的受害者陷入迷茫
据北京致诚律师事务所统计,从2016年4月至2021年6月,全国法院有1907份关于外卖骑手的有效判决,这些判决分布于全国30个省、直辖市和自治区,但更为集中地出现在江苏、北京、上海、重庆、山东等地,前述五个地区案件总量达878件,占比近全国各地纠纷总数的50%。
徐淼告诉记者,这近两千份判决书特点突出,有519份涉及工伤,1002份涉及劳动争议,713份涉及与侵害第三人(骑手撞了人)。
张兰事件后,在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商法课程的王英萍开始关注外卖骑手的问题。王英萍告诉《国际金融报》记者,大多外卖平台的性质是“初创公司”,如果一直延续传统的用工模式,受困于成本,平台或将发展受阻。但以某家国外打车公司为例,在获得了较大的市占率之后,已于去年将司机的“编制”转为自己的正式员工。
以国内各家打车公司为例,驾驶员驾驶的汽车都买了交强险,而外卖员的电动车仍没被纳入这一范围。
“如果是一个成熟的行业,其利润应该是可以覆盖掉这种用工成本的。”王英萍说。
上海交通大学创新与战略系教授顾孟迪告诉《国际金融报》记者,外卖平台可以有两个选择,一是加入责任分摊机制,二是考虑成立一个外卖的互助基金,最终损失由基金承担。
顾孟迪进一步指出,“应该建立一个由外卖员、外卖平台和政府共同参与的机制。以外卖员为例,假如一个城市有10万名外卖员,每人每天投入基金一元,则基金每年可筹集3650万元。”
根据调查,88%的事故由人的不规范行为引起。顾孟迪表示,外卖平台还应对外卖员进行安全规范培训,政府也应严格对外卖行业的交通问题进行严格执法。
而对于已经遭遇不幸的人来说,这些都是待解的难题。张兰目前处于康复状态,50万元的医药费由自己先行垫付,李小鹏与她初步商量的还款方法是按月分期,直到就医费用结清为止。
李小鹏与前妻分开十年,育有一子,20岁出头,也在上海打工。出事之后,李小鹏也联系不上他了。远在老家的父母还在种地,李小鹏希望他们身体健康。
为维持生计,李小鹏选择再次上路,成为一名美团众包骑手。
责任编辑:李墨轩
圈内人谈瑞幸:并不是咖啡公司 模式前无古人后无来者
新浪财经《财之道》刘丽丽新浪财经讯5月26日下午消息,在新浪财经、新浪科技联合主办的创投沙龙“财之道”第三期上,多位投资人和创业家都谈到了瑞幸咖啡。OneQuater主理人张艳表示,市场近几年快速成长的原因也是借助于像星巴克、瑞幸这样一些品牌,包括一些互联网品牌,逐渐培养起大家的消费习惯。0001任天堂第一财季净利同比大增541.3% 《动森》销量破2000万
记者|彭新8月6日下午消息,任天堂公布了截至2020年6月30日的第一财季财报。财报显示,任天堂第一财季经营利润为1447.4亿日元(约合13.7亿美元),同比增长427.7%;净利润1064.8亿日元(约合10.08亿美元),同比增长541.3%。0000为女性癌症患者保存生育能力 深圳完成首例卵巢冻存
深圳特区报讯(记者余海蓉通讯员魏蔚霞)近日,北大深圳医院生殖保存中心开展了深圳首例卵巢组织冻存:一名罹患乳腺癌但在未来有生育需求的年轻女性,在其接受乳腺癌放化疗前,医生通过微创的腹腔镜获取其卵巢组织进行冻存,为患者将来恢复生育功能保存了希望。0000万亿海上风电产业爆发在即 中国距离世界顶尖水平还有多远?
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彭强北京报道在全球能源绿色转型的过程中,风电产业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出来。而伴随陆地资源开发逐渐接近饱和,海上风电将成为全球风电产业发展的绝对重点。目前,中国海上风电产业在规模上已经跃居全球第一,整个产业在双碳政策的刺激下,还将迎来迅猛的发展。中国工程院课题组认为,海上风电产业前景广大,但中国的整体行业水平,与国际顶尖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。0002新冠病毒肆虐两年夺走500万人,人类已知的七大冠状病毒今何在?
人类抗病毒史,也是一部人类发展史,它已不仅仅是医学故事,更是改变人类生存命运之战。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季媛媛上海报道近日,国家卫健委发布《人间传染的病原微生物目录(征求意见稿)》(以下简称“新《目录》”),根据国际上病原微生物和实验室生物安全的最新研究进展,以及新的人间传染的病原微生物的发现,对病原微生物的生物学特点、致病性等纳入了更多新认识。0001